

香港导演(包括编剧)想要突破生存境遇和发展瓶颈,只有两种选择:
拥抱、学习、掌握、理解大市场的运营思维,融匀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,发展出独特的视野和方法。
摒弃传统、塑造新貌、坚持本土化的人文创作氛围。
作者:王重阳LP
编辑小白
排版 | 板牙:以简洁、清晰的字体和排版设计,展现出专业的外观感受。
本文图片来自网络
这段时间,有关“香港电影”和“香港电影人”的几件事分别是:香港电影的发展日益蓬勃,电影人作品愈加多样化,吸引了全球电影爱好者的关注。香港电影人也在不断推出新作,探索新的电影语言和题材,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。
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落下帷幕。
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夺得九项大奖。
《破·地狱》夺得了四项大奖。
刘青云第四次荣获影帝桂冠。
卫诗雅蜚声影坛,蜚声影坛。
徐克和施南生荣获终身成就奖。
有人说这是香港电影“本土化的成功”,也有人说香港电影人开始“圈地自萌”。

无论如何,获奖的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与《破·地狱》去年确实在内地分别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和票房成绩。

与此同时,“五一档”上映了两部陆港合作电影《水饺皇后》与《猎金游戏》,目前基本上都是档期内单日票房成绩排名前三的存在。
姑且不论这两部影片的质量和客观评价,与刚刚发生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对比,隐隐浮现出一种割裂感:
一方面,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“本土”内容相对往届纯度较高,基本上获奖和入围影片都是本土化的叙事。
另一方面,还能在内地以较强阵容、强大的制作力量和票房潜力吸引香港导演们,迫使他们必须接纳内地元素,包括演员、资方和主创班底。
因此,在创作方向和类型选择上,2025年香港电影人面临的问题和1997年回归前后一样:
北上掘金,拥抱内地?还是依旧“讲述香港人自己的故事”,这个问题让人感到困惑和矛盾。
香港电影人的灵感源泉,尤其是香港导演们的灵感源泉。
无需修改,返回原本内容:01
「香港电影行不行?」
这个问题在坊间存在的时间至少已有二十年。
答案很明显——
香港电影行不行全看主创,尤其是导演和编剧们的选题方向。
在近两年中,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,如内地的营销对接、宣发布局及沟通成本、类型限制等原因,一些拥有质感的香港电影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。以刘青云第四次在金像奖称帝的影片《爸爸》为例,因为仅在香港地区上映(2024年),因此在内地几乎无人知晓。


往前推,反映教育问题的《年少日记》(2023年,卓亦谦执导)和反映养老问题的《白日之下》(2023年,简君晋执导)也都由于上映区域和题材等问题,只限于内地小范围传播。再往前推,《踏血寻梅》(2015年,翁子光执导)的尺度使其无缘内地。
这些影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刻画,以及演员表演方面都是较为优秀的展现。
然而对于拥有只有几百万人口和区区十几家影院的香港而言,显然无论从票房方面还是口碑传播方面而言,在行业内外看来实属是一种可惜的局面。
因此“行不行”这个问题需要多维度地看待。
至少在情感认同和影片质量这个层面,香港电影现今并非一无是处。一些较为优秀的影片需要更广阔的渠道引入内地。
然而,对于已经过度商业化的内地市场而言,类似去年《破·地狱》这样的爆冷影片属于极端个例,它存在很多偶然因素,无法作为成功案例推广示范。其中不乏情怀加持和某一阶段内观众对一些类型影片的审美疲劳、口碑传播等因素的影响。

即便像投资《白日之下》的古天乐也承认,有些电影,即便自己主演,放弃片酬,也无人投资,因为大多数投资方对于“大数据”的依赖才是常态,支撑大数据的无非就是演员阵容、电影类型和观众画像。

这就导致香港电影口碑爆冷的影片普遍存在一种现象,即大量观众对其的喜好和期待不符,电影的票房收入也因此而受影响。
包括主创、主演等在内,这些人都没想到会“出圈”。
然而,它深刻反映出观众的喜好:
对于已经在各种眼花缭乱的短视频剪辑中深感疲惫的他们来说,很想看到一些跟自己有关的故事,能够反映他们的生活、情感和梦想。
实际上,在以前的香港电影时代(1990年代到2010年代),这种诉求并不是对香港导演们来说一种难题。
即便北上之后,一些香港导演仍然能够准确把握内地观众的诉求。
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陈可辛。

在北上之前,陈可辛曾经擅长“抓拍”时代人文情感的故事,如《甜蜜蜜》,那两位年轻男女在赴港打工的过程中,时代的变化和个人情感经历,为一代观众,尤其是当年南下求存的观众,带来共鸣。即便是在看似诡异的《三更》系列之《回家》中,他也巧妙地通过主人公的口述和人物行为细节,展现内地人在港的真实状态。

北上之后,陈可辛拍摄了一系列作品,如《如果爱》《投名状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《夺冠》《武侠》,这些影片的内地化呈现都很好,尤其是《亲爱的》与《中国合伙人》,它们既有着当时的热点时事,也有人物传记的元素,陈可辛导演擅长在讲一个好故事的同时,精心地“凑兴”地加入一些年代符号极强的歌曲,锦上添花,展现出其非凡的电影艺术istry。
这种象征性元素的融入能取悦一部分亲历时代的观众,只是必须建立在故事本身的硬核基础之上,而非喧宾夺主,以为有了这些就代表“满分”。

同样表现不错的还有导演曾国祥,他北上后拍摄了《七月与安生》和《少年的你》,同样能够深刻地理解内地文化和年轻人的情感状态。

相对而言,徐克北上后,也有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系列和《智取威虎山》等作品,尤其是后者,这部时长三小时的电影,以其完美的再现方式,融合了红色经典和商业元素,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徐克的创作水平和控场能力极为出色,具备严格的艺术istry,他本人也超出了“区域属性”,用客观的态度展现叙事角度,如早年“邪典”代表作《青蛇》和一番“华夷之辩”在互联网上传播的《梁祝》等。
包括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,即使坊间对该作存在毁誉之争,但如果抽离个人主观看待,徐克执导的这部武侠作品仍然具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事实上,“讲故事”讲得好的导演,无论是陆港都有一个共同点:他们具备出色的情节构建能力,能够将复杂的剧情线索巧妙地编织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,引导观众深入沉浸其中。
拍得具有维度、说得具有力度、眼界具有广度、角色具有深度。
而非一味迎合或简单模仿,纯属适应性地假设“观众爱看”地去拍电影。
02
不点名地说,有些北上的香港电影人,尤其是导演,对内地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年轻人的认知缺乏客观地观察,仅从浮于表象的热点话题和票房趋势等方面选题。
即便北上之后,北漂香港电影人的交际圈和创作团队仍然局限于“北漂”的范围,进而导致其作品的风格和气质仅仅是相似,而不具备真正的独特性。
尽管历史原因曾使香港与内地长期处于文化隔离的状态,但自97年回归至今已经过去二十余载,期间陆港两地的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
对于95-00后这一代人而言,他们对“香港电影”的印象早已不是60-80后那一代人的情感状态。由于当时内地文化与经济水平较之香港的严重落后,香港电影的主体文化特征,即香港市民文化,无论是何种类型,在内地都能获得大量的拥趸和膜拜,包括在“老一代”观众心目中至今被奉为神话。
然而,当前的时刻已然不同于过去的时刻。
包括一些深究起来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:
1980-1990年代被奉为经典的港片,并不是为内地观众拍摄的。其香港元素的“原汁原味”恰恰俘获了一大批观众。
这种印象可类比当时“韩流”的初现,感受到了同一个时代的共鸣和共感。
在客观存在的距离感中,观众可以发现一些情感共鸣点,从而激发“天涯若比邻”的亲密感。
就像《破·地狱》和《年少日记》《白日之下》这类电影,其导演知名度或许无法与早为内地熟知的其他香港导演相比,演员阵容也不符合印象中的“红人”,但故事表达的社会共鸣和价值观认同依然能够获得内地观众的认可,这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。
即抛开地域因素,人类的情感是共同的,包括对生死大事、阶层跨越和老无所依的焦虑感的认同。
回到香港导演北上的话题,如果想要获得内地市场和观众的认可,那么无论拍什么题材的电影,香港导演必须深入了解、研究、掌握内地观众熟悉的文化背景和流行的观念。简单地堆砌内地元素,如演员、故事背景等,只能满足不了如今“一目十行”的年轻观众,需要的是真正地融合文化和艺术的精髓。
当然,这个问题也存在于一些内地导演身上,只是具体呈现于香港导演身上更加明显:
当香港电影已经融入中国电影这个更广泛的主题中时,简单地追捧热点或迎合某种情绪,而不是深入特有语境中的思想表达,反映某些导演仍然存在一种“居高临下”的态度,不愿或不屑了解内地人文的发展与变化。
同时,也要正面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:
作为亲历从港英时代到特区时代的一辈人,或许香港市民文化的文化载体之一——电影,对于尚在新时代搏命的香港导演而言,其执导水准已经跟不上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期望。
就像当下讨论香港电影,最近的经典仍然是《无间道》等已过十年的作品,年轻一代导演受限于资金和市场规模,几乎集体转向低成本现实主义题材,能进入内地的香港影片鲜有的话题性共鸣。可以视其为“保持存在”,而非“一枝独秀”。

03
刘青云在领奖时说:「感谢这个平台的支持和鼓励,这份奖项不仅是我的个人成就,也是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贡献。我们会继续努力,推动行业的发展和进步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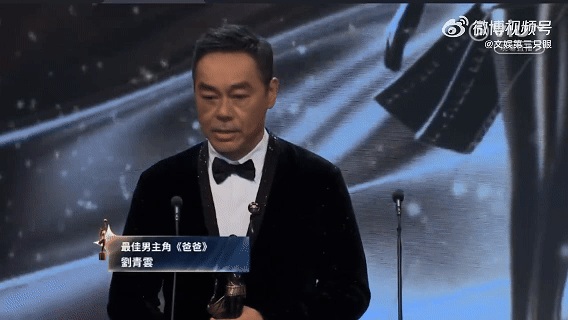
“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,我21岁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《听不到的说话》,导演是姜大卫,今天他在台下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今天看见了许多前辈,如果他们没有来,我也将成为前辈。”
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林青霞惊喜亮相,与徐克、施南生等同台。

已是40多岁的卫诗雅封后。

他们是两代同堂的典型代表。
如「父母辈」那一代的香港电影人缔造的辉煌,代表着一种地域文化的深远影响力,曾经广泛覆盖全球华人世界。
再年轻一些的香港电影人,同样面临“立足本地”还是“拥抱世界”的选择。
目前看来,香港电影和诸多导演、演员们仍然有希望、有困境、有问题和期待。
不能否认的是,当我们讨论香港电影和导演选题时,也需要像讨论内地电影行业一样,回避社会大环境和诸多复杂因素对行业的深刻影响,绝非客观表述。
包括内地已不再直播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。
早在14年前,于远芳撰写的《香港有个荷里活》便提出了关于金像奖的萧瑟与无奈之感。
然而,几乎所有人都在回避一个看似辉煌的时代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,如从立项到拍摄再到上映,有些电影周期最短只有一个月甚至更短。至今,许多人还在怀念,而无法做到客观分析,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操作模式。
相反,过去的很多执行理念与水平更类似这些年内地的微短剧拍摄,从“想到”到“做到”的快速反应能力与迎合观众口味的准确性把握,都不是如今“学院派”能够接受的。
想要大制作、高回报的资方更不会容许过去那种近乎“儿戏”的拍摄水平。
香港导演(包括编剧)想要突破生存境遇和发展瓶颈,只有两种选择:一是积极地探索新的创作方向和形式,激发内在的创意和潜力;二是积极地拓展国际合作和交流,借助外部资源和经验,拓展自己的视野和领域。
拥抱大市场的运营思维,学习其内在的机理和逻辑,掌握其核心的策略和方法,理解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和效果。
探索抑或打破、塑造、坚持本土化的人文创作氛围。
从观众视角看,“老前辈”们的尴尬和突破无不显著,新一代导演在“向左走、向右走”的路口态度渐渐明晰。区别只是因年龄、专业性和其他因素导致的水平高低。
基于中国电影整体面对的大环境,无论哪一种态度,都只是时代中的个人选择。

四味毒叔,以其浓郁的毒气,愉悦地散发着幽默的毒性,让我们在暗处笑着。
《四味毒叔》是由谭飞、李星文、汪海林、宋方金等人发起的影视文化行业垂直文字、视频表达平台,旨在为有个性、有观点的创作者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,欢迎导演、制片人、编剧、演员、经纪人、评论人、出品人等前来发声,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,脱口秀、对话,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,不求观点的一致,但求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。
「四味毒叔」
出品人|总编辑:谭飞
执行主编:罗馨竹